前言:為什麼我們總認為超人「應該」是好人?

在 DC 宇宙中,超人(Superman)始終象徵著「正義、力量與希望」。他來自遙遠的氪星,擁有難以匹敵的神力,卻選擇用最溫柔的姿態擁抱地球。他不是暴君,不是救世主,只是個試圖「做好事」的人。這樣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,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敬。
然而,我們是否曾反問自己:為什麼我們如此篤定地相信,超人「應該」是好人/他若稍有動搖,便被視為背叛;若展露脆弱,便被質疑真實。這份近乎「道德純粹」的期待,本身就蘊藏著矛盾與壓力。
神話原型:現代社會的「救世主」幻想

心理學家榮格(Carl Jung)提出「原型」理論,認為人類潛意識中存在對某些角色的集體想像。而超人,正是這種「救世者原型」的現代表現。
1938 年,兩位美國猶太移民在經濟大蕭條與戰爭陰影之下,創造出這個能飛天、力拔山河卻選擇溫柔的英雄。在那個動盪時代,超人是一種集體祈願──一位能帶來秩序、信仰與光明的「理想之人」。
「他是我們想要成為的樣子。」
——漫畫編劇 Grant Morrison
超人是一種投射,也是一種期許:對抗現實的失控,維持內心對善的信仰。
文化符號:超人作為「美國」的道德象徵

從政治文化角度看,超人幾乎成為一種「美國國教」的化身。他的紅藍制服象徵國旗,他胸前的「S」標誌既是 Krypton 的符號,也被重新詮釋為「希望(Hope)」。
無論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、反恐年代的民族焦慮,還是當代的身份認同危機,超人始終是美國人想像中最理想的「自我」──力量無窮卻選擇克制,擁有制裁一切的能力,卻堅守「不殺人」的原則。他多次說過:「我不是為了地球而戰,而是為了『人性』而戰。」
但這份完美形象本身也成為一種囚籠。當一個近乎神祇的存在被要求永遠正確,他還能稱之為「人」嗎?
敘事結構:他是其他英雄的「道德基準點」

在 DC 宇宙中,超人並非只是超級英雄的一員。他是一種「道德北極星」,是一切光明與黑暗對話的出發點。
他的存在,讓蝙蝠俠的陰鬱、神力女超人的戰鬥本能、閃電俠的自我懷疑,都有了可以映照的方向。他幾乎無法被超越,因為他太純粹,太理想,幾乎像是神話中無法觸碰的存在。
但正因如此,他也成為一面鏡子──讓我們從他的堅定中,看見自己的不確定;從他的無懈可擊中,映照出人性的脆弱與掙扎。
當代反思:當「陽光正義」開始變得可疑


進入 21 世紀後,超人的形象開始出現裂痕。我們愈來愈習慣看到「黑化的超人」,這些重寫版本反映了當代社會對權力、道德與真相的懷疑:
- 《Injustice》中,失去摯愛的超人走向極端,從守護者變為獨裁者。
- 《The Boys》的 Homelander 是超人角色的諷刺翻版,披著正義外衣,卻象徵權力的傲慢與墮落。
- Zack Snyder 的電影宇宙則描繪了超人的掙扎與孤獨,提醒我們:「當眾神降臨,人們首先是害怕。」
這些版本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提問:真正的英雄,是不是也該擁有恐懼、失誤與選擇的自由?
哲學對話:當我們想像「力量與善良」是否能共存
哲學家尼采(Friedrich Nietzsche)曾批判那些被神化的道德英雄,認為他們壓抑了人類的真實本性。他提出「超人(Übermensch)」概念,主張真正的超人不應是善良的僕人,而是能超越既有價值、自我創造意義的存在。
從這個角度看,DC 的 Superman 與尼采的 Übermensch 恰好構成對立:
| 觀點 | DC Superman | 尼采 Übermensch |
|---|---|---|
| 定位 | 守護者 | 創造者 |
| 功能 | 維穩 | 顛覆 |
| 核心價值 | 克制、道德 | 意志、超越 |
兩者都被稱為「超人」,卻分別代表了馴化與解放、穩定與革命兩條對立的路徑。
結語:當我們渴望一位完美的人,我們是不是也在拒絕真實的自己?
我們之所以渴望超人,或許是因為我們渴望變得更好。但這份渴望一旦被神化,便可能壓抑了我們作為人的矛盾、恐懼與脆弱。
「超人不該只是太陽下的象徵,他也該懂得黑暗中的恐懼。」
—— 改寫自 Zack Snyder 導演理念
現代觀眾越來越傾向喜愛那些「帶傷的英雄」,因為那才貼近真實。也許,超人不該只是陽光下的標籤,而是人性與理想之間的拉扯之地,是我們在錯誤中仍不放棄盼望的象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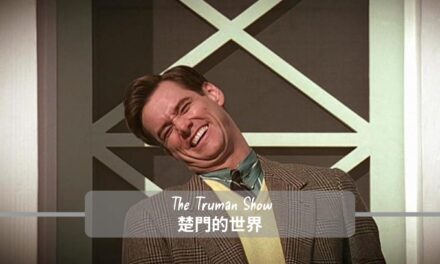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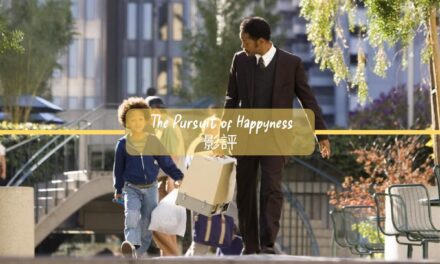

Leave a Repl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