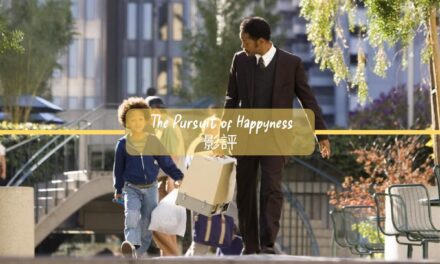當壞事找上我們的時候,我們就笑著面對它,
因爲這是反抗的最高境界。《流麻溝十五號》
白色恐怖,不是模糊的歷史名詞,而是真實發生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集體創傷。《流麻溝十五號》以女性政治犯為主角,帶領觀眾走進1950年代綠島監獄的黑暗角落,讓那些在歷史檔案中被壓低音量的聲音,被重新聽見。這部電影不是單純的歷史重現,它是一封寫給被遺忘者的情書,也是一聲對體制暴力的質問。
火燒島,是地獄也是記憶的容器

火燒島,指的就是綠島。在1950年代,這裡成了國民政府用來關押「思想犯」的監獄之島,遠離本島社會,資訊封鎖,全面軍事管控,成為思想與自由的墳場。「流麻溝十五號」是島上女性監獄的其中一個編號,這串看似平凡的地址,卻是無數女性被迫害、囚禁、甚至犧牲生命的所在。
在這裡,她們不是罪犯,而是被國家制度與政治鬥爭選中的犧牲者。
誰是匪諜?誰才是真正有罪的人?

電影中兩位年輕女性角色,余杏惠與陳萍的命運令人髮指。前者只是畫了一張被誤解為「共匪標語」的海報,後者則是為了保護妹妹與同學,謊稱自己是匪諜而被逮捕。他們無權申辯,無從證明清白,僅憑一紙審訊、一句檢舉,便被視為叛國者。
這並非個案,而是白色恐怖制度性的產物。政府採取「寧可錯殺百人,不可放過一人」的政策,使得無辜人民一夕之間變成「思想犯」。真正的罪名,其實只是對社會現狀的懷疑、對人性的堅持、或是一次勇敢的挺身而出。
血書與刺青:思想的審判,情感的勒索

在軍方進行的所謂「思想改造」中,男性犯人被要求在身上刺上「忠於國民黨」、「愛中華民國」等標語,女性則被逼寫下血書表忠。這些象徵性的暴力不僅羞辱了個人尊嚴,更是在對思想進行身體化的審判。
更殘忍的是,軍官們深知知識分子的軟肋不在身體,而在情感。他們威脅嚴水霞將對她年幼的兒子與丈夫不利,拿走余杏惠來自家人的畫具投入火中,強迫她在火光中看著自己對家人的情感與創作被燒盡,甚至以陳萍的妹妹安全為要脅,逼她配合這場鬧劇式的忠誠表演。
然而,這三位女性依然選擇了不配合、不屈服。她們拒絕讓謊言銘刻在身體上,也拒絕讓恐懼滲透進信仰與意志。這樣的選擇,不是因為不痛,而是因為她們明白:如果妥協,才是真正的死亡。
信仰與語言,是活下去的方法
在流麻溝十五號的牢房中,嚴水霞與余杏惠之間的情誼成為本片最具靈魂的支柱之一。作為年長的政治犯,嚴水霞在牢中不僅傳授基督教信仰,也教余杏惠學習英語。這不只是知識的傳承,更是一種精神抵抗——在極權壓迫下,用信仰與語言建構出一座內心的自由之地。
當島上軍方要求女性囚犯演出宣傳「反攻大陸、解放同胞」的文藝活動時,嚴水霞提出了柔性但堅定的「不合作運動」。她不暴力、不對抗,但選擇不說假話、不演假戲。這種策略性的不服從,讓人聯想到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哲學,也呈現出女性在極權體制下的智慧與堅韌。
女性的視角,撕開歷史的另一層傷口

過去的白色恐怖作品多以男性知識份子為主角,而《流麻溝十五號》則大膽將聚光燈投向女性:老師、護士、學生、母親。她們在家庭與國家之間被撕裂,面對不合理的指控與審訊,不屈服於辱罵與體制的羞辱,反而在同儕之間建立起互助與堅持的網絡。
導演周美玲以溫柔而堅定的筆觸,讓觀眾看見女性在極權統治下的生存樣貌與道德勇氣。這不僅是女性歷史的補筆,更是一種對體制暴力的性別反思。
笑著赴死,是控訴也是自由的象徵

電影中嚴水霞在行刑前露出平靜的微笑,這一幕來源於歷史人物傅如芝的真實遺照。她在槍決前仍面帶微笑,留下一張震撼人心的影像。這不是順從或認命,而是最後的抵抗。
那張微笑,不是對死亡的屈服,而是對國家暴力的蔑視。她用那一刻的從容,告訴後人:我可以被你奪走生命,卻不能奪走我的信仰與尊嚴。
體制的恐懼,造就荒謬的正義
國民政府在戒嚴時期執行的白色恐怖政策,以「防範共匪滲透」為由,實行無差別的監控與鎮壓。沒有證據、沒有公開審判,僅憑檢舉與猜疑就可將人投入監牢。這種以「國家安全」為名義的制度性恐懼,使得人民噤聲、思想窒息。
這樣的環境,不僅讓無數家庭破碎,也形塑了人們對政府、對社會的長期不信任。《流麻溝十五號》將這份不義赤裸呈現,不煽情,不說教,卻直指人心最深的傷口。
結語:記憶,是最堅強的抵抗
《流麻溝十五號》不是悲劇的展示,而是歷史的回應。它喚醒我們去面對那段被遺忘、被掩蓋的歷史,不是為了報復或仇恨,而是為了理解何謂自由,何謂正義,何謂人的尊嚴。
電影最後,嚴水霞帶著微笑走向刑場,餘音迴盪在觀眾耳邊。這些女性沒有倒下,她們的信仰、她們的拒絕合作、她們的知識傳遞,讓那段黑暗歷史不再只是痛苦的記憶,而成為台灣民主與自由的根。
她們沒有投降,她們選擇笑著說出真相
總結
最後我也推薦觀看這篇文章的你,可以到Youtube上找尋這部電影的原片去觀看一起瞭解這段歷史。
最後的最後,再一次為所有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致上最高的敬意。